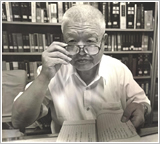
【编者按】史树青,1922年8月16日生于河北乐亭县。1935—1941年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。当代著名史学家、文物鉴定家。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,国家博物馆研究员,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,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导师,被誉为鉴定国宝的“国宝”。
在文物鉴定行里,花很少的价钱买到很大价值的文物,叫做“捡漏儿”;过目即知真伪、价值几何的鉴定文物的学问,称为“眼学”。史老的收藏品都是史老从报国寺、潘家园等处的地摊上“捡漏”捡来的便宜货——卖的人看不出这些东西的价值所在,心里都把它当成破的、假的,走低价蒙着卖。史老鉴定文物不借助科学手段,全靠“眼学”,过目即知真伪。在已过目的上百万件文物中,重要文物的鉴定,史老从未出过错;至于小件文物的鉴定成功率,史老戏称是95%左右。在书画、碑帖、金石、青铜、瓷器、古籍等诸多鉴定领域,史老均达到很深的造诣,被称为文物鉴定的通才。
从小到现在史老一直在捡漏儿,而眼学也就修炼了一辈子,乐此不疲。
史树青在8岁大时跟着父亲来到了北京。他父亲做绸缎生意,余暇很喜欢收藏字画,尤其喜爱故乡人书绘的作品。耳濡目染,史树青也喜爱上了文物鉴定与收藏。
1935年,14岁的史树青从扶轮小学考进了闻名遐迩的师大附中。作为北平城最好的学校,不仅设备好,而且同学好——个个是翘楚。先生们就更好了,像教国文的孙照先生、李兰坡先生、王述达先生,个个学识渊博眼界高,治学教学有专长;张鸿来③先生,甚至自编教材授课。附中的国文教育为史树青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。
放学以后,史树青三天两头去琉璃厂,不是到海王邨买旧书看,就是到古董店挨个踅摸踅摸。在日复一日的来往中,他和古董店的老板们都混熟了。听着他们讲古玩文物的故事和鉴宝的规矩,史树青慢慢熬炼着自己的眼力。当时北海公园的国学书院每周开课,请当时的著名学者讲授经、史、子、集、书画艺术,史树青是当中最最年轻的学子。
1937年春节。史树青没怎么逛厂甸庙会,一拐弯又来到了琉璃厂,路边有很多临时搭棚子支摊卖字画、小摆件的。有个棚子里所卖书画的纸色看着并不久远,所以顾客寥寥。但史树青依然走了进去,一幅一幅作品地看起来。其中有一幅书法立轴吸引了他:“夜来忽忆儿时事,海沸天翻四十年。心绪如潮眠不得,晓星残角五更天。”那笔力真是遒劲。落款是:“戊申年五月二十八夜作 邱逢甲②”。卖主认为字写得倒是不错,但就是作者无名,这卷立轴能卖个三两毛钱就行。史树青心中暗喜,邱逢甲怎是无名之人呢?好读文史书籍的他,清楚地记得邱逢甲是台湾爱国诗人、抗日的义士。15岁的史树青掏两毛钱买下了这卷立轴,由此捡到淘宝经历中的第一个漏儿。
从那以后,史树青越来越觉得:要捡漏,不记住人名、不了解其基本经历是不行的——至今,史树青已经记住了5000位以上的古今书画文人的名字及其主要事迹。
七七事变以后,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城。师大附中被日本兵强占为养马场,尘翻土扬,臊臭难当。学校说没就没了,老师们、学生们生生被遣散了。部分老师绝不肯在日本铁蹄下苟活,内撤到西安等地继续办师大附中。时读初三年级的史树青被迫转到了育英中学。虽然育英中学挺不错的,但史树青觉得从方方面面来比的话,还是附中好!
1938年,日本骑兵终于搬出了附中所在地。附中的教学又恢复了!该上高中的史树青立即返回了附中。先生们在课堂上虽然不明白地宣示抗日,但是个个借古讽今,托物言志,暗暗激励着自己的学生勿忘国耻、坚忍爱国。日本侵略者虽然允许附中恢复办学,但是规定日文是必修课,并派来了日本老师。学生们知道日本人的用心,学是学的,就是不用心学。同学们间偷偷流传着这样的话:“日本话,不用学(此处读“淆”音)。再搁三年也用不着。”大家盼呀,盼着日本侵略者早灭亡,亡国奴的日子早结束。回想那奇耻大辱、命悬一线的8年,附中最引以自豪的是,老师中、学生中没有出一个汉奸!
虽然兵荒马乱,史树青在放学后还是经常去逛琉璃厂。他把捡漏儿买来的字画拿回学校,给张鸿来、孙照几位先生看。有时先生们不在自己的办公室,史树青就直奔他们的宿舍。史树青对这几位四五十岁的老夫子毕恭毕敬,但却没有距离感。因为字画,先生们给他单独开辟了第二课堂;因为字画,他和先生们成了忘年交。史树青和先生们在一起,听他们品评,和他们共同鉴定,多有滋有味啊!
史树青鉴定字画的经验日渐积累着:鉴定书画不但要研究画的主体,就连细节,比如落款、题诗和印章等等,都得一一注意。一般的书画在唐宋时期是不落款的;到了宋朝以后,画作上就题上了作者自己的名字,或者注明绘画的内容和绘画的要旨。卖造假名人字画的人,往往是把小名家的名字去掉,自己给补写一个大名家的名,这叫去本款,小名家的画作就变成大名家的了。绘画作品的质地也是鉴定时特别需要加以思虑的。画作的质地有的是绢底儿,有的是纸底儿。同一质地的纸与纸又不一样。明朝纸就有棉纸和麻纸之分,大不一样。做假画的,会把新纸染成旧颜色以显得年代久远。作假明朝的纸,一种把白纸染成麦黄色,一种是染成老鼠灰的颜色。做假的不但染纸,还会染卷……
有一次,张鸿来先生的朋友从琉璃厂买到了一幅郑板桥的画《竹石图》,顺路到附中找张先生帮着鉴定一下。一件东西要是假的,通过挑毛病来否定它,比较容易。一件东西要是真的,找证据确定它,就不容易了。可画到底是不是郑板桥的真迹呢?张先生不能确定,其他几位先生也不能确定——这么犹疑不决也不是事啊。张先生就把史树青找来了。
史树青拿过画,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后,坚定的说:“是真的。”
“你能确定这就是?现在市面上仿郑板桥的赝品可不老少啊。”
“能确定。您看这画中的画笔、书法运用得多流畅而无滞碍啊。这是真迹。我家里有郑板桥的字、画。我认真琢磨过啊。我也读过郑板桥的书。我有经验。您看这年代也对得上。”
先生们虽然见他说得这样有底气,但鉴定书画到底凭阅历、凭“眼学”。先生们还是建议买主拿画到琉璃厂,找研究郑板桥书画的行家鉴定鉴定。行家一看,确实是郑板桥的作品。从此,史树青在附中、在琉璃厂可就有了名气啦,许多别人看不准的东西也就纷纷来找史树青鉴定了。
从上高中起,史树青还利用课余时间到北海团城的国学书院上课。书院每周开一次课,请当时著名的学者讲授经史子集、书画艺术。学生每月要交反映学识长进的两首诗、两篇古文的作业。史树青是当时学生中最年轻的一个。
1941年,史树青从附中毕业了。离校前,亦师亦友的先生们都题诗相赠史树青。张鸿来先生的题诗是:“书画常叫老眼花,鉴藏年少独名家。纵同文奕犹贤已,莫误含英与咀华。”这诗中的前两句道出了老先生对史树青的鉴定书画水平的嘉许;后两句既表达了老先生引史树青为知己的忘年交情,也包含了对史树青一定要继续深造学习的殷切期许。
同年,史树青考取了辅仁大学④的中文系本科生,在自己所喜好的文学方面继续深造。在辅仁大学,史树青又遇到了几位人生中的良师益友。
余嘉锡⑤先生,当时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。为了维护国家民族正气,余先生特意开设了《楚辞》课,教育青年识别“香花毒草”,以抨击当时的卖国求荣者;开设《世说新语》课,对魏晋之际崇尚清谈而误国,反复推理,评论古人而讽喻时事,寓意深远。
陈垣先生⑥,当时是辅仁大学的校长。他根据书的内容和用途,把要读的书分成了三类:即一般浏览、仔细浏览和熟读记诵。有的一两天就翻过去了,有的要读上个把星期,有的则需翻来复去地背诵。这样一来,陈先生泛读的书比一般人多,精读的书比一般人深。许多基本史料,他不用翻检原文就能引用,给治学和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。他建议史树青搞鉴定一定要学历史。
在师从余嘉锡、于省吾、陈垣等先生的过程中,史树青不仅对目录学、版本学有了深刻的认识,以便于今后鉴定古籍,而且学会了巧读书。史树青鉴定哪一件文物不是靠文献记录提供线索,或是作证据呢?到晚年虽然戏称自己真正读过的只有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,就连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也没读全;但是在实际上,史树青真正做到了读书破万卷,“鉴宝尽书源”——史树青会做“书皮的学问”,简而言之就是一本书,不一定页页翻读,字字深析,关键在于一定要记住书的名字,谁写的,什么时候写的,是什么版本,书中的主要内容是什么,特别是要把目录背下来。只有这样才会尽可能减少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的遗憾!
与余嘉锡、于省吾、赵万里等先生接触,兼修美术系启功、溥雪斋的课程,使史树青的兴趣与眼学扩展到了金石、古籍、铜器等领域的文物鉴定上。
1945年,当史树青从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,又开始读历史学研究生。当时他还在汇文中学教书。1946年史树青应沈阳一所大学邀请去做中文系讲师。他又成了沈阳古董店的常客。当时许许多多的故宫国宝都流散在沈阳的大小古董铺中。不少好古董,不是日本人在中国连抢带买,投降后没来得及带走的文物,就是古董商从伪满“首都”长春买来的,溥仪从故宫带出的珍藏——其中一幅清代的《四季花卉》到今天仍让史树青记忆犹新。史树青也曾建议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赶紧组织收购,但是苦于经费不足,这些国宝大多还是被有钱的收藏家买走了。史树青作为一个穷教员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文物的流散。不过,他在那里又学到了不少东西,增长了眼学功力。
1947年在余嘉锡先生的推荐下,史树青到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(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)工作,从此一直工作到2002年80岁时退休。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50多年间,史树青始终抱定爱岗敬业、刻苦学习的宗旨,遵照国家文物局对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要求,以“制度健全,帐目清楚,鉴定确切,编目详明,保管妥善,取用方便”为工作方针。不但协助领导出色完成博物馆收集、保管、陈列及宣传教育等工作,还指导青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,培养提高业务水平。
1950年天安门举行庆祝“五一”劳动节游行,大家先要到西直门集合。史树青那天去得很早。在好多卖早点的饮食摊当中,有个老太太正用一个青花大盘子(有炒菜锅那么大的口径)盛着凉粉叫卖。史树青远远看着,就觉得那盘子颜色好,花样好,像是个古董。史树青就跟同行的王世襄走了过去,凑近一看,竟然是明朝初年官窑烧制的青花瓷。俩人当即就要买下来,老太太说:东西好不好,不懂。可这个盘子确是件祖上传下来的东西。俩人央告了半天。老太太说:得,给五万块钱(新版人民币发行后,折合五元钱)吧。他们俩翻兜凑钱买了下来。俩人高兴,抱着大盘子站队,抱着大盘子游行。一路上,引起许多人驻足观看。俩人这才觉着别扭,顺道存在裴文中先生家,后来贡献给了故宫博物院。
1952年,史树青捡到了一生中最有历史价值的一个漏。史树青的有个小学同学,她丈夫是民国时期蒙疆使者陈宧的儿子,叫陈仁恪。陈仁恪为了贴补家用,要卖些旧书画,就找到了当时在京城文物收藏界已经鼎鼎大名的史树青。书,主要是一些元朝史书,没什么特殊价值。一幅成吉思汗的画像半身引起了史树青的特别注意。在史树青记忆中,成吉思汗画像过去见世仅有一幅,还是明朝人仿制的;而这幅画中人物的服饰与《元史?舆服志》中的记载相吻合。虽然他当时不能一下子就确定这是不是元朝的画作,但他觉得这幅画中肖像应该很接近真人相貌了。史树青花几元钱买下了这幅旧画,然后就捐献给了历史博物馆。这幅画曾经过几次认真地鉴定,1962年张珩、谢稚柳、启功、徐邦达等专家再一次作集体鉴定,确定是画匠在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凭着记忆绘画的,是元朝时期祭祀用的画像,应该列为历史博物馆一级藏品。这幅画像的发掘,不仅突破了博物馆成吉思汗的文物实品的零记录,更有着广泛的社会价值,它作为现存最早的成吉思汗画像被广为引用,我们中小学的教科书中也总是拿它作为重要插图。
史树青还经常随考古队,奔赴全国各地去考察鉴定。1958年他参加中国科学院新疆少数民族社会调查,曾至乌鲁木齐、喀什、和阗、民丰、伊犁、塔城等地调查少数民族历史,编写简史、简志,参加哈萨克族简史、简志的编写工作。
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,史树青曾参加了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遗址参加发掘,河南郑州二里岗商周战国遗址发掘、山西侯马遗址调查等等。其中,以1980年调查、鉴定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群最引世人瞩目。
历史上人们一直认为孔望山石刻的内容是孔子给弟子讲课。而史树青考察后认为是早期佛教造像群。它以释迦牟尼涅槃,弟子举哀为题材。开凿的年代为东汉,比敦煌石窟还要早200年,是目前我国已经发现的最早的佛教石刻。这一新发现,对中国雕刻艺术史、中国佛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,都具有重要开拓意义。后来经过申报,1982年国务院批准孔望山石刻群为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在社会工作之余,史树青勤于笔耕,他的主要著作有《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》(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年出版);《天安门》(与人合著,北京出版社1957年出版);《祖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瑰宝》(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出版);《应县木塔辽代秘藏》(与人合著,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);《楼兰文书残纸》(天津古籍书店1991年出版);《小莽苍苍斋清代学者法书选》(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);《中国大百科全书?文物卷》(与人合著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出版);《中国文物精华大全》(与人合著,1995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);《书画鉴真》(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出版);《鉴古一得》(于1999年学苑出版社出版);主编《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》(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)等。
由于深厚的文史知识底蕴、丰富的鉴定经验,史树青从20世纪60年代起担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教授,南开大学历史学系教授,还长期在中央民族大学讲学。从1973年起他还多次担任中外文物交流的主要负责人,对外弘扬中国文化传统。
史老即使到了退休年龄,依然热心地为馆内征集文物。1997年有个河北省大成县的人到历史博物馆来鉴定、出卖一个腰牌。接待的人看了看腰牌,说:“现在社会上假的文物已经有不少了。这个也是假的,不值钱,我们不要。”那人正磨叽呢。史老刚好进门:“这是什么东西?给我看看。”接过东西一看:银质鎏金的一块腰牌,长21.7厘米,宽6厘米,正面和背面分别铸有汉字和契丹文——“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”,是蒙古国皇帝颁发诏敕的信物。史老把那人拉到一边,说:“你先别走,我请你吃中午饭”。吃饭当中,就问他:“多少钱买的?”“八千块钱买的,你们给我点儿赚儿,给我一万……九千块钱,我就卖给您了。”“这个东西,我跟他们研究研究,……您先吃完饭再说。”到下午了,史老把馆长请来了,馆长一看:“假的。不能要。”史树青当时没有决定购买文物的权力,就留心把卖腰牌的地址记下来了。
为了这块腰牌,史老又找到国家文物局的张文彬:“张局长,你得帮忙啊。好东西,成吉思时代的,还不称汗。这可是真的。您一定给河北省文物局局长打电话,腰牌现在河北省大成县。河北省不要,咱们要,这东西是个国宝啊,不能放了啊。”张文彬局长给河北省文物局去电请他们征集,卖腰牌的人认识到奇货可居,立即把价钱涨到了两万多块钱。河北省方面嫌贵而没有要。最终,还是张文彬局长出面花了两万五千块钱给买过来,送到了国家博物馆。
回想这件事,有些“聪明人”不理解:既然博物馆馆长都已经发了话,“腰牌是假的”,那么史树青当即只花个八、九千元钱自己收藏了这件文物,不仅名正言顺,而且心安理得。可为什么史树青宁可得罪许多博物馆界的人、费尽周折也要为国家博物馆得到这块腰牌呢?
每提及此事,史老心平气和地解释道:“这个东西是给博物馆的,不可以个人自己要。就怕给公家送来了东西,你看着好,自己收了——这是道德的问题,职业道德的问题,犯罪的问题。咱不能做。” 说着说着,史老激动起来:“我们陈列室里陈列成吉思汗这位政治家的文物,就有一个成吉思汗的画像,底下什么成吉思汗的用具、纪念品啊,什么都没有。这儿来一个硬货,这还了得吗?我们追求博物馆的文物,追求了50年了。我们征集成吉思汗的文物上哪儿征集去,没有啊。征集过来就是陈列的需要啊。这么好的东西能自己要吗?”
这块圣旨金牌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惟一的一件成吉思汗文物实品;不仅如此,史先生对这件文物进行细致的考证后,做出一个重要的历史论断:铁木真在世时,不仅是称汗,而且已经称皇帝。如果这个论断成立,那么蒙元早期封建化的历史就要进行重大的改写。
几十年来,史老把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都献给各大博物馆了,自己家里收藏着什么呢?3万多册古旧书籍——这是史老觉得最宝贝的,这是他“眼学”的源泉之一啊。其次是几百张字画,这里面有地摊上捡漏捡来的,更有沈从文、启功先生等书朋画友相赠的作品。再有就是几把古剑。
2005年4月,史老在北京大钟寺文物市场的地摊上,发现一把青铜剑颇为“眼熟”,剑身菱形暗纹,并有一些绿色的锈迹,上有两行错金的鸟篆体文字“越王勾践自作用剑”。“有价值!”史老花1800元钱把这把古剑买回来。
回到家中,史老对这把剑进行了研究,发现剑的底部一面镶有青金石,另一面镶着绿松石,剑柄上还有 12个同心圆,这种装饰在先秦古剑中常见。史树青让家人拿出几张报纸,手握寒光闪闪的宝剑,轻轻一划,叠加在一起的数层报纸瞬间被切开,露出整齐的切口。
史老眼熟的这把古剑,其实与他缘份颇深。1965年12月,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把古剑,该剑出土时寒光闪烁,纹饰清晰精美,通体无锈迹,震惊考古界。郭沫若、于省吾、商承祚、史树青等专家汇聚湖北,破解古剑密码,确认为越王勾践的王者之剑,即“越王勾践剑”,并且被专家公认为“天下第一剑”。时年41岁的史树青是当时与会最年轻的专家。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《古剑》,记录了史老鉴定古剑的场景。
1973年,史老操办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化展”赴日本及欧洲展览,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由他亲手带到日本东京展出。后来为保护原剑,曾复制了两把越王勾践剑,复制品都没有错金(错金就是古代铸剑时在剑身上开槽刻字后,用黄金做成的细丝镶嵌在所刻字的凹槽)。
“而这次我买的这把剑在文字上更好,使用了错金工艺,所以价值当在那把剑之上,应该为一级文物”。史老认为这把剑虽然是民间传下来的,但确实是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配剑。这把剑的历史价值应该与当年闻名全国的夫差剑相上下,论市价起码可以卖到上百万元——当年勾践的子孙的一把佩剑还拍卖了104万元呢。史老对于这种级别的古董是一定要上交的。
史老把剑送给了国家博物馆。可是博物馆方面却认为这是假的,拒收。史老很不开心,写下了这样一首诗:“越王勾践破吴剑,鸟篆两行铜错金。得自冷摊欲献宝,卞和到老是忠心。”史老让自己的孩子把那个摊儿上其他几把剑也都买回来了,先收藏着。
2006年,史老从地摊上又捡漏买到了一件宋代的瓷瓶,是哥窑制作的“金丝铁线”。史老这次要把它献给故宫博物院。故宫博物院虽然很客气地派来两个年轻人登门相见,但是来人认为瓶子是假的,婉言谢绝了。史老又伤了一次心。
国宝不能回家、进入国家的博物馆固然让史老伤心、着急,但更让史老伤心的是:自己看着是真的国宝,年轻人为什么就看不出来呢?是自己老眼昏花了呢,还是自己满肚子的学问没人懂,无以为继了呢?
史老自己的不少弟子已经弃学经商去了。虽然能理解“他们也要生存”,但是在史老的观念中,做学问就是要专心做,参与了商业活动是会耽误研究学问的。做文物需要专业知识,要有眼力,抱着发财的思想,急功近利,肯定要上当的。现在能安心读书钻研专业、创新提出独立见解的学生太少了!
耄耋之年的史老还在为文博鉴定事业的未来忧心忡忡……
(根据中央电视台《大家:访文物鉴定家史树青》、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《艺林漫谈 征史探源鉴真宗》、人民日报海外版《文物大家的鉴藏人生——访著名文物鉴定收藏家史树青》、北京娱乐信报《我读的书还是太少——史树青:我鉴定的正确率是95%》、北京青年报《人弃我取,点石成金》、每日新报《史树青——鉴宝识英雄》、《国学网》余嘉锡、陈垣相关网页等综合改编。)
?张鸿来(1880—1962年),字少元、邵元,天津人。教育家、版本学家、书画家、文物鉴定家。曾任北平师大附中校长。1962年去世,其30余年的藏书赠送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,其藏书中以天津乡邦文献、小学音韵著述为特色。
④北京辅仁大学:1925年由中国天主教领袖英敛之等创办的一所天主教大学,1927年开始招生。日本侵占北平期间,各国立大学相继南迁,日伪托用这些校址相继建立伪大学。辅仁大学由于是罗马教廷天主教会下令创办的,当时由德国神甫主持校务,使得日伪有所顾虑,成为不受日伪支配的独特学府。1952年夏,辅仁大学的主体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,组成新的北京师范大学。
⑤余嘉锡(1884-1955年),字季豫,号狷庵,湖南省常德县人。国学大师,语言学家,文献目录学家,史学家,精于考证。曾任清朝吏部文选司主事。1927年参加审阅《清史稿》。在北京、辅仁等大学主讲目录学。著作有《目录学发微》、《古书通例》、《四库提要辨证》、《世说新语笺疏》以及《余嘉锡论学杂著》等。1947年以《四库全书提要辨证》一书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。解放后,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。
⑥陈垣(1880—1971年),字援庵,广东新会人。国学大师,历史学家﹑教育家。无师承,靠自学闯出一条深而广的治学途径,可贵地尝试把传统史学方法嫁接到新史学主干上。在宗教史、元史、考据学、校勘学、年代学等方面,著作等身,成绩卓著,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。对敦煌文书、明清档案等新材料的整理和研究有杰出贡献。他重视教育事业,1926~1952年,任辅仁大学校长;1952~1971年,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,任教四五十年间,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,影响深远,造就了众多的人才。